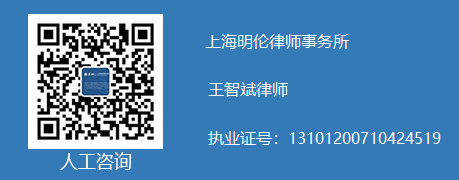深大通案股民胜诉,督导机构被判担责,“首恶”成“主犯”
深大通案股民胜诉,督导机构被判担责,“首恶”成“主犯”
近日,投资者诉深大通证券虚假陈述案迎来一审胜诉判决。该系列案因对督导机构责任认定、“收购暴雷”型虚假陈述责任划分的突破性裁判,成为资本市场法治领域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案例。
该案聚焦重大资产重组后标的公司造假引发的虚假陈述争议,在持续督导机构责任认定上打破既往裁判惯性,在责任分担上确立“首恶全责、比例连带”的精细化规则。
一、督导机构责任认定的突破:重组关联性视角下的义务穿透
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持续督导机构的责任认定一直是司法难点,深大通案对中信华南证券责任的判定,恰恰突破了此前“仅对直接督导事项负责”的裁判逻辑,核心逻辑在于锚定了督导机构与虚假陈述源头的“重组服务关联性”。
该案中,中信华南证券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深大通收购视科公司这一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又是重组完成后的持续督导机构,而案涉虚假陈述的直接根源,正是收购标的视科公司在重组交易阶段即已存在的财务造假行为。
法院审理明确,中信华南证券作为重组阶段的财务顾问,核心尽职调查义务应覆盖标的公司定价公允性、核心盈利能力、财务数据真实性等关键要素;作为后续持续督导机构,其督导义务天然延续对重组标的经营合规性与财务真实性的监督职责,但其仅通过象征性访谈、形式化培训等方式履行督导义务,未发现视科公司的系统性造假行为,最终判令其对投资者损失承担3%的连带赔偿责任。
这一裁判逻辑与深圳中院审理的索菱股份虚假陈述案形成鲜明对比。在索菱股份案中,招商证券仅担任持续督导机构,其督导范围未涵盖索菱股份年报虚假陈述所涉的核心财务事项,且未参与相关重大资产重组的顾问服务,法院最终认定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两案的核心差异在于“责任关联度”的界定:深大通案中,督导机构的“重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机构”双重身份,使其对造假源头的标的公司自始负有穿透式核查与持续监督义务,虚假陈述事项属于其核心服务范围的延伸;而索菱股份案中,督导机构与虚假陈述行为无直接服务关联,仅负有一般性程序性督导义务。
深大通案的裁判创新,核心在于确立了新的裁判规则,为督导机构履职划定了明确边界。如果证券服务机构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担任财务顾问,其后续持续督导义务不能局限于程序性文件审核,而应穿透至标的公司的持续经营状况、财务数据真实性等实质内容。这一裁判导向将直接倒逼督导机构强化全流程履职管理,在重组尽调阶段即建立标的公司动态跟踪机制,从前端防控重组标的造假风险,为资本市场重组交易的合规性提供司法保障。
二、责任划分的创新
深大通案的另一核心突破,在于针对“收购暴雷”型虚假陈述构建了“首恶全责、主体区分、比例连带”的责任划分体系,打破了此前部分案件中“上市公司全额兜底、中介机构责任模糊”的裁判模式。
该案审理中,法院精准界定各主体责任边界:视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夏东明作为虚假陈述“首恶”,其直接组织实施虚构广告业务的造假行为,是导致深大通年报虚假记载的根本原因,故判令其对投资者扣除系统风险后的损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上市公司深大通虽非造假直接实施者,但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对收购标的尽职调查存在疏漏,法院考量其“收购暴雷”的间接受害属性与自身直接造假的本质区别,酌定其对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审计机构中汇所因存在风险评估不当、函证程序缺陷等重大过失,承担30%的连带赔偿责任;中信华南证券因过错程度较轻,承担3%的连带赔偿责任。
这一精细化划分模式与传统虚假陈述案件形成鲜明对比。在上市公司直接主导财务造假的案件中,法院通常判令上市公司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中介机构按过错比例承担连带;而在早期“收购暴雷”案件中,常出现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原股东责任划分模糊、中介机构责任轻重不分的问题。深大通案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匹配”原则:一方面坚守“追首恶”的监管导向,明确标的公司原控制人作为造假主导者的核心责任,避免上市公司因“被动造假”承担过重责任;另一方面细化不同主体过错层级,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义务不可豁免承担主要责任,中介机构根据履职缺陷程度承担对应比例责任,实现“罚当其过”的裁判效果。
这一责任划分规则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对上市公司而言,明确了“主动造假”与“收购标的造假”的责任差异,倒逼其强化并购重组中的尽职调查质量,建立标的公司财务核查长效机制;对中介机构而言,责任比例与过错程度的直接挂钩,推动其完善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在重组尽调、持续督导、审计鉴证等各环节强化风险防控;对标的公司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而言,“首恶全责”的裁判导向形成强力震慑,从源头遏制其利用重组交易实施造假的动机。
作者:王智斌律师团队
执业证号:13101200710424519